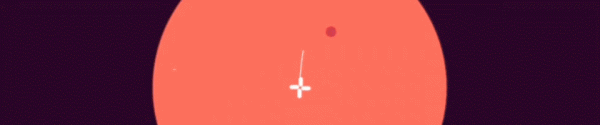正规长沙配资平台
正规长沙配资平台
软件教父,退出江湖?

近日,一份最新发布的股份变动公告显示,东软已悄悄换帅。
曾有着“软件教父”之称的董事长,职务变更为荣誉董事长,而荣新节则出任公司的董事长兼CEO。
东软的头上,曾经叠加着无数的光环。
它是国内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,早在1997年,便斥资5亿元,投资建设国内第一个软件园。
同年,东软研发了国内第一台临床应用CT机,打破了海外垄断的局面。

只是,随着刘积仁退居幕后,这个昔日无比辉煌的企业,走向也愈发模糊。

1988年初,刘积仁与另外两名老师以3万元科研经费、3台286计算机创建了“计算机网络工程研究室”。
时年33岁的刘积仁,是中国首个计算机应用博士,也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。
在当时中国软件产业几乎空白的背景下,他以\"架设学术与产业桥梁\"为愿景,依托高校资源研发本地化软件技术。

之后,团队开发的\"计算机网络协议软件”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,吸引了国际关注的视线。
1991年,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寻求汽车软件外包伙伴,刘积仁团队凭借技术实力,以3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订单。
利用这笔资金,双方一拍即合,成立了软件研究所,对日外包成为早期生存的“输血线”。
90年代末,中国启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。
东软凭借技术积累,中标多省市社保系统建设项目,成为全国社保信息化核心供应商,市场占有率超50%。
由于业绩快速攀升,东软顺势在1996年6月上交所成功敲钟,顶着“A股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”的桂冠,募集资金1亿元。

之后,东软乘势而上,业绩喜人。
2005年,全球软件外包业务中,中国占比2.3%,东软成为中国最大的离岸软件外包提供商。
2006年,成为国内第一家外包收入过亿美元的软件企业。
不过,时代的红利,往往是昙花一现。
早期,东软依靠低成本工程师红利,承接日韩、欧美外包订单,但随着国内人力成本上升,薪资年均涨幅超10%,其价格竞争力被印度、越南等新兴国家分流。
加上技术附加值低,外包业务集中于低端代码开发、测试维护等层面,而在云计算、AI驱动的自动化开发浪潮下,传统人力外包需求逐渐萎缩。
东软长期依赖为政府、国企提供本地化系统集成,但2015年后,政企客户全面转向阿里云、华为云政务云服务等平台。
政策红利消退,东软错失云转型关键窗口期。

对比用友、金蝶等对手2015年启动云转型,东软直至2020年才推出“东软云”
2020年,其云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5%,而用友、金蝶等对手云服务占比已超50%。

对于软件外包的弊端,刘积仁早有察觉,因此很早之前就带领东软进行了多次转型升级。
2009年,东软正式进军健康管理服务领域,且陆续成立了医疗子公司或与外企合资建立合资公司。
2010年,东软进入开发汽车与消费电子领域。
2015年,东软和老朋友阿尔派合资成立东软睿驰,主要为汽车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。

介入自动驾驶、辅助驾驶等领域,还成立了专门针对车险的保险公司。
经过多年发展,东软集团已成为拥有医疗健康、智能汽车互联、智慧城市和企业互联四大板块的巨头,外包业务变得乏善可陈。
不过,智能化转型并不容易。
在医疗、汽车、城市和企业服务赛道,东软都有强大的竞争对手。
劲敌环伺之下,东软压力山大。
2022年,东软集团经历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。
营业收入为94.66亿元,归母净利润为-3.429亿元,同比下滑129.23%。
面对困境,刘积仁选择拥抱人工智能,用业绩进行回击。
2024年初,东软启动了解决方案智能化战略,积极打造智能化、数据价值化、服务化和生态化的解决方案。

而在智能汽车互联领域,东软集团拿到了比亚迪、长安、长城等国内诸多主流厂商的订单。
同时,布局马来、越南等地的企业服务业务,业务规模也实现了翻倍增长,企业互联的营收增长达到26.59%。
2024年上半年,东软集团扭亏,实现营收净利双增。但两年的扣非净利润仍为亏损,分别亏损1.473亿元和3613万元。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业务营收同比下滑。
一直以来,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业务,毛利常年维持在40%以上。
但2024年上半年,医疗健康板块的营收同比下滑了8.22%,占集团营收比重从24.39%降至16.05%。

虽然整体数据上有升有降,但多元化发展并没能给东软带来业绩上的高增长,反而暴露出核心战斗能力的不足。

近年来,东软集团不断分拆子公司,被市场诟病是以登陆资本市场为目标,认为其”想赚快钱“
早在2011年,东软集团将IT高教业务剥离,成立东软教育,2020年成功登陆港交所,上市首日股价大涨超过25%,市值达到45亿港元。
之后,东软医疗、东软熙康和望海熙康又分别进行分拆,其上市目的已经昭然若揭。
东软熙康历经四次递表后才在2023年9月登陆港交所。上市首日,东软熙康破发收跌43%。

东软医疗和望海康康目前仍在筹备上市。
与阿尔派、沈阳福驰共同投资成立的专注于自动驾驶研发的东软睿驰,在2021年完成6.5亿元融资后被独立分拆,目标也是登陆资本市场。
除此之外,东软的并购之路走得也颇为曲折。
通过控股望海康信,孵化熙康、收购韩国Samsung Medison等,试图构建大健康生态。
但望海康信盈利波动、熙康持续亏损且IPO遇挫,Samsung Medison未助其突破高端市场。
东软收购哈曼汽车软件,令东软在2014年收购该公司后获得了奥迪、宝马的订单,但利润率低于8%。

2017年,东软收购阿尔派电子,强化了自身的IVI系统,但未能解决芯片依赖问题。
2020年收购Commando,其车联网安全技术应用于东软睿驰,但未形成规模。
这些收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软汽车电子板块的营收占比,2023年该板块营收占比提升至25%,但毛利率仅18%。
低于德赛西威的24%,且收购未解决高价值环节的自主能力问题,智能驾驶布局落后于华为、德赛西威。
东软收购神州新桥时,神州新桥承诺2019—2021年净利润2.1亿,实际仅完成1.6亿,完成率76%。
2022年计提商誉减值3.5亿元。
好在2022年,业绩有了一定的增长,到了2024年,神州新桥营收54.42亿,净利润1.67亿。

总体而言,东软的收购历史呈现”散点布局多,核心突破少“的特点。
收购战略缺乏技术主线牵引,更像被动补漏,而非主动构建能力护城河。
东软的困境,本质是中国第一代技术企业的集体缩影。
当依靠政策红利与行业空白期建立的优势,在数字化时代被对手瓦解时,如何在AI的热潮中,聚集于核心业务,提升公司的创新和盈利能力,或许是东软新的掌舵者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参考资料:
1.连线insight:《东软,正在失去想象力》
2.数智研究社:《百亿东软集团,什么钱都想挣》
3.牛刀商业评论:《东软换帅!‘软件教父’刘积仁交棒荣新节,太意外了》
作者:胡南
编辑:歌
灵菲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市配资交易论坛 中国队全员金牌,团体冠军横扫2025 IMO!满分学霸曾在北大蹭韦神课
- 下一篇:没有了